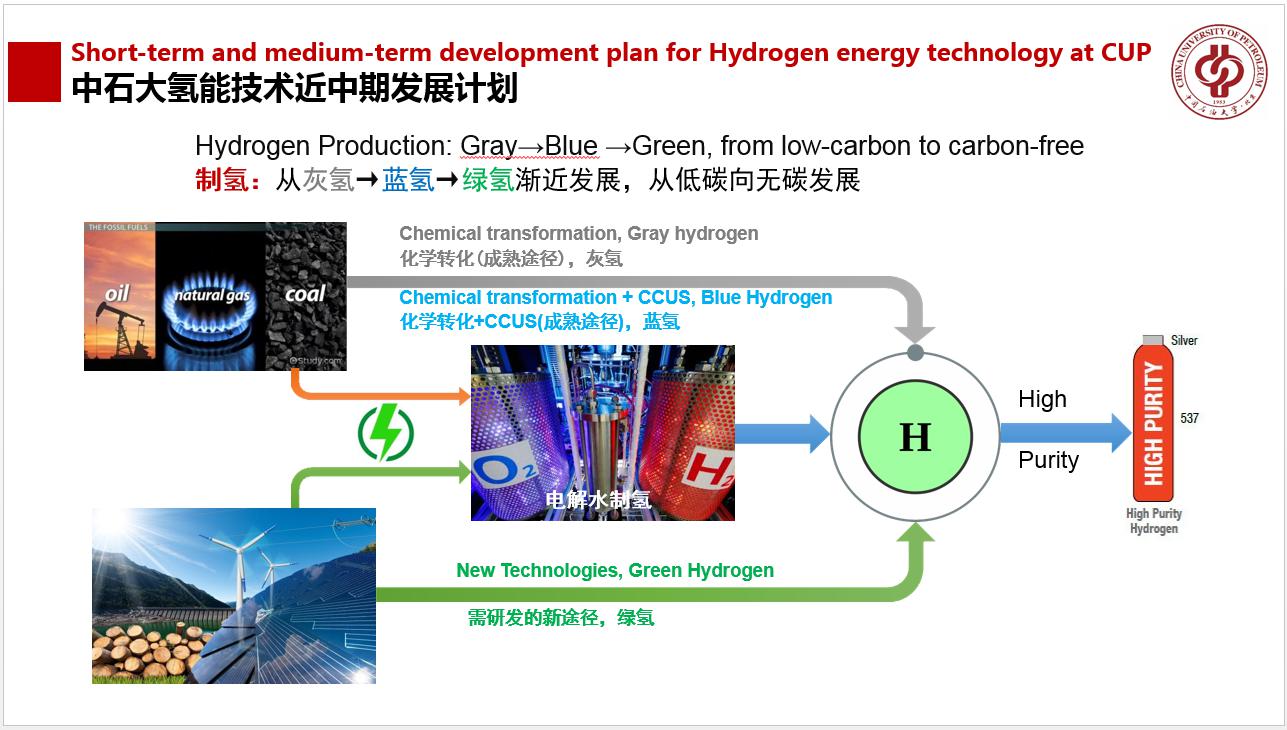
编辑按:2024年11月30日,东京经济大学主办的“绿色转型决定产业未来”国际研讨会在东京召开。在第一场专题讨论“中日绿色转型实践”上,日本环境卫生中心理事长、原日本环境事务次官南川秀树,澳门城市大学教授、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原司长徐林,IMF原日本代表理事田中琢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登台探讨了中日两国在绿色转型(GX)领域的政策和成果,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
首先,曾经担任东京经济大学客座教授的南川秀树原日本环境事务次官指出,环境污染一般能够特定造成问题的主体和受损主体。但是气候变化问题则不同,大规模二氧化碳排放会对所有国家产生均等的影响。也就是说,排放主体与受损主体之间可以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对排放主体不容易施加压力。在前不久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声希望实现经济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给予他们支援。关于这一点中日两国都在积极努力,当然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需要向世界传播正在如何推进减排对策。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澳门城市大学邱晓华教授指出,中国正处在数字转型、智能转型和绿色转型的三大转型过程之中,力求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国经济目前整个发展的大趋势,这些转型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
邱晓华强调,世界百年大变局其实从两方面给中国提供了挑战和机遇。一方面是地缘政治的调整与变化,使中国正面临着来自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中国也还面临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传统产业方面的挑战。
关于中国的绿色转型,邱晓华表示,中国政府提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并出台了包括构建碳排放的双控制度体系,推广可再生能源,推动节能降碳改造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的保护,促进经济结构的绿色化,创造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省的社会。这些做法已经取得了明显变化,例如截至2024年8月底,中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占总发电装机规模的40%以上。今天的中国天更蓝了,水更清了,空气更新鲜了,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正在不断改善。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原司长,中美绿色基金徐林董事长强调,中国是一个把绿色低碳转型上升到生态文明高度的国家,这在全世界并不多见。而且中国确实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例如从增绿的角度来说,中国在过去40年左右的时间里把森林覆盖率从12%~13%提高到了25%,相当于增加了100万平方公里的绿色空间,接近日本国土面积的3倍,这个工作量与投资量都是非常大的。目前中国森林覆盖形成的碳汇达到12亿吨,相当于中国一年碳排放的十分之一左右。
徐林指出,在推广新能源方面,特别是风能、太阳能、核能的发电量在急剧增加,这一进展在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环境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徐林表示,随着中国的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和成本在不断下降,在这个领域做投资已经可以盈利,不再需要政府补贴。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发现,绿色低碳转型在中国已经不是一种压力,而是可以带来相当大增长的投资机会。所以绿色低碳转型其实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动能。
田中琢二IMF原日本代表理事就日本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说明。日本政府提出到2030年要将温室气体削减至2013年的46%,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到2030年日本需要将2013年14亿吨的CO2排放量削减至7.6亿吨。其中能源产生的,特别是发电产生的CO2减排是关键。发电产生的CO2的减排将占到减排总量的一半,这需要依靠大规模导入再生能源才能得以实现。
田中琢二强调,中日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在经济发展上继续深化合作。中日两国正在推进新能源技术和碳定价制度方面的合作,在这些领域日本借鉴了许多中国的先进举措与经验。
田中琢二还表示,日本非常重视扩大新能源的导入和下一代技术的研发,南宫28官方网站特别是海上风力发电和氢能的技术研发、蓄电池制造供应链的强化、下一代太阳能电池的研发等。碳定价和新的金融手段也是支持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机制,是吸引民间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与脱碳的重要保障。为确保社会公平,对弱势群体和地区的经济支持不可或缺,气候变化对策要兼顾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
作为点评嘉宾,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指出,南川先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气候问题不但危害严重,覆盖全人类,而且这个问题非常难。难就难在造成气候变暖的主体跟受损主体之间,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有着极大分歧。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迅速赶上来的工业化国家和没有开发的国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所以这个问题是人类面对的一个极大难题。南宫28官方网站
周其仁点评,与会嘉宾们分别介绍了中国和日本应对气候挑战,实施绿色转型的经验,这两个国家无论从国家战略目标,国民理念,具体政策措施都在绿色转型方面创造了大量有益的,对全人类来说有帮助的具体经验。
邱晓华认为,虽然从数字上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但是从人均角度来说,中国从经济水平、人均碳排放水平来看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一方面,中国会积极参与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要求和呼唤,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也会积极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新型能源,治理环境,发展新产业。第三,中国也会在人才培育方面给国际社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定的支持和帮助。
徐林指出,中国第一是要把自己的碳排放控制程度做得更好,中国有可能提前实现碳达峰,也有可能提前实现碳中和。中国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多贡献,在碳减排领域,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中国有很好的技术可以很好运用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低碳能源转型过程中去。从一名投资人的角度来说,把中国的新能源技术用在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低碳能源替代方面是有很好的投资机会,所以并不一定都需要政府援助资金去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碳减排。
周其仁强调,要尽最大努力防止把气候、减排问题变成国际政治摩擦、冲突、搞名堂的题材,要尽最大努力把它转化成国际经济合作,国际共同创新的新型挑战的题材。要说服各国人民参加,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总要拿一些看得见效果的项目来落地,这有助于说服更多的人。
针对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球性的降碳减排,田中琢二表示希望大国领导之间能够尽快达成推动应对气候挑战的框架协议。
对此周其仁回应,问题是现在大国领导人当中有人根本就不认为气候变暖是一个趋势,那怎么谈得拢?要谈不拢,那怎么可能达成一个全球性的协议?人类到今天还没有说对任何重大问题都靠协定来解决,还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很多地方还在打仗,虽然有联合国,世界照样天天在打仗。多少万人的生命在消失,这样的问题也谈不成,何况像气候这种长期性的问题。所以首先要降低对达成一个全球协议框架的期望,哪一个国家、哪里的人们、哪个团体认识到应对气候挑战这个事情应该做就开始做,可能是一个现实务实的道路。





